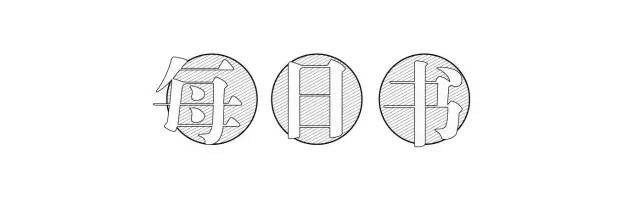在经历过几场反复的倒春寒之后,广州的夏天悄然而至。不知道从哪个夜晚开始,窗外出现了细微的虫鸣,到了凌晨四五点的时候,鸟也苏醒了,间或发出啾啾的叫声,他们隐匿在黑暗里,像齐齐在等待日出,等一个万物苏醒的时节。
广州一直不是一个四季很分明的城市——除了漫长而炎热的夏季以外,其他季节好像都没有一展风采的机会,反而更像交替出现、争奇斗艳的伶人,譬如春天里落满一地的黄叶,又譬如冬日里间或飙升到二十来度的气温。其他时候,广州多被闷热、潮湿的氛围笼罩,所谓的四季,倒更像是只有夏、冬两季了。
而自疫情以来,因为被困家中,就更难觉察出季节的更替和变换。
二月以来,大部分人都被禁足在家。邻里间的嫌隙、家庭里的矛盾,都像暗中滋长的藤蔓,把人心束缚得越来越紧。有时天刚亮没多久,便能听到楼下的中年妇女的咒骂声,骂的是不知几楼的邻居,浇花滴下去的水把她刚晾的衣服全淋湿了,她骂了好几次,说“你不要太过分了”“说了好多次了,怎么还浇?怎么还浇?”,然后声音渐渐隐去,想是已经去拍楼上邻居的门了;有时到了夜晚的时候,约莫十点左右,又听到不知哪家的男孩子发出躁狂的、歇斯底里的嘶吼,想是和家长起了争执,是青春期里积蓄在身体里的无限逆反之力,混合了对绝对自由的向往,也许是声音太大了,反让人听不清他在吼什么,但总归是涕泪横流的,好像拼尽了全身最后一丝力气那样。
在这相对静止的时间和空间节点里,只有这些声音还在提醒我,日复一日的、漫长的琐碎生活,匍匐在自然节气之上,又是那样无意地塑造着广州城,一春又一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