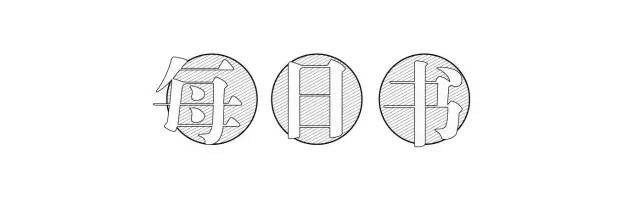人们常说,蛰居在一处久了,语言风格、行为举止,便越来越接近当地的民风民俗。对一座城市最强烈的爱意,可能就是自豪地宣布自己是哪里人,是话语间不可磨灭的硬气。
我不是一个喜爱挪窝的人—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便是这样给自己下定义的。高考的失利并没有让我如愿以偿地考上北京的大学,而是辗转到了武汉。那应该是我从小到大离家最长久的一次独居。但在这之前,在我离开广州之前,我也没有那样强烈的意识,认为自己就是广州的一份子。
我始终是太不像一个南方人了。从小到大,没有一个人觉得我具有南方人身上的一丁点特征。身高未免太高了些,脸盘也太大了些,就连嗓音也不够柔软细腻。我活脱脱是北方人的后代,只是恰巧在南中国的土地上出生、长大,仅此而已。我的母语不是粤语,粤语是我在读幼儿园的时候向同学慢慢学的;在最开始的时候,我的普通话字正腔圆,能明确地区分平翘舌音、说话还带儿化音;我结交了一些“北方血统”的朋友,并和他们保持着很好的关系,与土生土长的广州同学,却始终保持着一些距离。
在我短暂的青春期里,我始终幻想北方城市应有的模样,有宽广但略显荒凉的街道,有成排的挺拔的白杨树,有凛冽的北风卷起地上的沙土,狠狠地拍打在行人的脸上。后来,便也得了几次机会,往那些向往的城市里去了几回,却不知为何,愈发愿意停留在广州。
我觉得人类是有惰性的动物,而我,就是拥有究极惰性的人——久居不愿动,一如长醉不愿醒那样,有时活在自己想象的梦里,有时又在做着生活在别处的美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