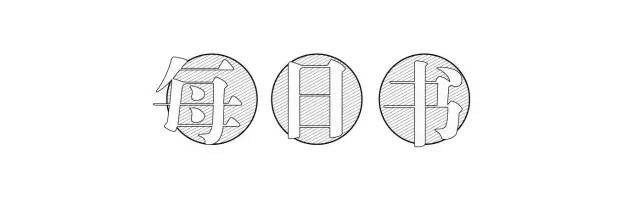每日书2020.5.19-5.24.
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,房子租在大埔墟,和一个北大女孩、一个中大女孩一起合租。这算起来不过50多平米的小房子里,住了3个人,我和中大女孩各占一间卧室,北大女孩睡在客厅,她的床只用了一个大书柜作为格挡,又在书柜和墙之间出入的地方拉了一道帘子。整个房子的租金是9300港币/月,这还是和房东谈了又谈之后的价格。
每天,我们三个人在这逼仄的空间里生活,虽然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不在这个房子里,但到了夜晚睡觉的时候,我们总要回到这里来的。
我的房间已经是两间卧室里偏大的那一个了——但它还是很小,小得只够放下一张转角的书桌和一张床。床和一个小飘台齐平,我在飘台上挂了晾衣服的绳子,平时洗好的衣服就晾在飘台上,有时候没拧干,衣服往下滴水,水就这样凉飕飕地落在床上。床也很短,短得连我168的身高都伸不直腿,睡觉的时候要斜着,腿要伸去飘台上。
每天夜里,我在这个小房间里看论文、准备演讲,临睡前总会撩开窗帘的一角,看看楼下的香港。我住18楼,到了晚上11点多的时候,周围的许多房子还是灯火通明,但楼下的街道上人却不多了,黄色的大箭头涂在冷冰冰的马路上,指示着车辆行驶的方向,但没有一辆车。
香港的楼宇,打开窗户总能听到很嘈杂而鲜活的风声,哪怕是很深的夜里,这种风也总是裹挟着一种难以言状的气味,一遍遍地敲打窗子,想要灌进房间里来。那种气味有点像面包房里散发出来的甜甜的味道,是一种会令人感到充实、欢畅的味道,在这个孤单城市的夜里,显得特别撩人。
但是和窗外这个喧闹的世界比起来,我的房间实在是太狭小和简陋了,也过分安静了。
在那个50来平的小房子里生活,就像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壳里,每个人在极其狭小的私人空间里各忙各的,有时候也会听到她们打电话的声音,隔着墙,模模糊糊的,像从遥远彼岸传来的信号。
当时签下这套房子的时候,我和中大的女生露露去中介办了很复杂的租赁手续,签了很多合同的同时,中介又复印了我们的证件,中介说了很多注意事项,尤其提醒我们不要损坏房屋里的家具,“也不要往墙上钉钉子。”他讲一口很市侩的粤语,是香港年轻人惯用的一种腔调,圆滑之中又有许多戒心和防备。原来,上一任租客就是因为往墙上钉钉子,让房东不高兴了。
房东是一个很年轻的女人,她当时的年纪,大概跟我现在差不多大,身材不高,保养得很好,在香港的德意志银行工作,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精打细算的聪明,有时我还没开口说话,她仿佛就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,又用别的话把我堵回去了。我觉得她很厉害,但不想跟她有过多的交集,只会每个月在交租后发短信告知她。她的回复永远是冷冰冰的、看不出感情的一句话:thanks,the rent is well received,有时候也发一个“:)”的笑脸。
住在客厅的北大女生叫阿哲,她的家在内蒙古满洲里——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的满洲里人,到现在为止,她也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满洲里人。有一次,她跟我谈起她的家乡,她说到了夏天的时候,草原非常绿,绿得无边无际,看一眼就忘却了所有烦恼。“冬天的时候,我们家包了饺子,就把饺子放在窗外的平台上,自然就结冰了,不需要冰箱。”她说。
她还跟我说了许多满洲里的事,勾起了我无尽的想象,当时我们站在那个小客厅里,她靠着书柜(那个隔断),我也站着,因为在这个简陋的小房子里,我们没有其他多余的座椅了,要么她站着,要么我站着,出于礼貌,我们只能一起站着,共同想象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大草原。
她说:“你以后一定要去一次满洲里,去了可以找我。我带你玩。”说完笑了,露出了两颗可爱的虎牙。
很多年以后的今天,我依然很难忘记那个房间,也很难忘记我们一起做过的那些梦,尽管毕业以后,我和她再也没有联系了。
在香港读书的生活,十分地两点一线。每天早上我坐接驳巴士到火车站,再坐东铁线去学校。火车行驶在地面上,时常能看到窗外飞驰而过的树木、田地,空旷而缺乏人烟,那是香港的另一面。路上虽然只有几个站,但总觉得十分漫长,因为下了车,还要换乘校巴,翻山越岭地去上学。
港中文建在山上,部分山路还颇有些陡峭,是巴士司机要狠踩油门才能上得去的。每次他踩油门的时候,车厢都会轻微地抖一抖,好像一个重新振作精神的野兽,准备对猎物发起新的进攻。每当这时候,我会想起大学时的校车——很巧合的是,我所读过的这两间学校都建在山上,爬山几乎成为了每天的必修课。
但武大的校车要更残旧一些,还经常因为学生太多、挤不下,而产生一种摇摇欲坠的危险感,上校车要花一块钱,或者刷学生卡。每到早上上课前,校车永远是满员的,湖北口音的司机总是骂骂咧咧,让大家再挤一挤,让出点位置来。这辆车开起来非常缓慢,再加上要爬一些很长的坡,就更显吃力了,晃晃悠悠地,每开几步就喘一下气。而车上的学生却显得耐心十足,好像也不太在意上课迟到——只要上了校车,它就总会载你到终点,虽然它老态龙钟、几近报废,但学生们却很信任它。
毕竟,如果不乘坐校车,就只能自己骑自行车或者步行去教室了。步行是一个苦活,从我们居住的湖滨,走路到校门口的教五,快则20分钟,慢则半个小时,途中要上坡、下坡,再上坡、再下坡。在武大文理学部骑自行车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,也有这样做的学生,但不多。
前两天和朋友吃饭,跟她说起在香港读书的时光,她说:“是哦,你家楼下的肥牛金针菇米线好好吃。学校食堂的港式奶茶也很正。”
但她说的,我都印象不深了,那段记忆好像受到了风沙的剥蚀,残存的只有一些零星的片段。
她来香港找我玩的时候,是请了五一节的假。那时候我基本没什么课了,有些同学甚至在收拾行李准备离港了。她住在我的小房间里,在床前仅余的两平方米的地板上打地铺,白天我们出去玩,晚上回来在这个小房间里聊天。这里从来没有那样热闹过。
我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,我躺在床上,用平板电脑去阅读艰难晦涩的英文文献,看着看着,觉得很困,手边还有很多纸质的课件要看,那些a4纸就这样凌乱地洒落在床上,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,刚洗好的衣服还在滴着水,在我耳边滴滴答答的,伴随着空调轰隆隆的声音,催我入梦。
一个人的生活,在缺乏自律的前提下,就会养成很多不好的习惯。我不爱做饭,因为那是个开放式的厨房,做饭会影响到在客厅的室友,实在饿得不行了就下楼随便吃点。那一年,我吃了楼下的麦当劳、过桥米线、三酱肠粉无数次。楼下还有一家甜品店,做一种名为“哈喽”的甜品,十分好吃,回广州之后在惠福路的甜品店再吃,已全然不是那个味道。
就好像现在再提起往事,也缺乏那些触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