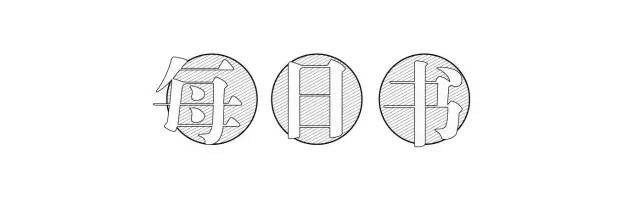这篇文章整合自我2020.5.5-5.7的每日书。因为同题共写的susu给这个月的主题定名为《异乡人》,所以我就循着这个题目开始写了。
《异乡人》这个题目,总令我想起加缪的《局外人》(一译也作《异乡人》)。想来总归是,局外和异乡,无非总是徘徊在事物的边缘,像一颗滴入水中的油,浑圆剔透,有自己的防御体系,本土化的事物入侵不了。油少了,便只你一颗,孤独怅惘;油多了,便形成一片网络,但和底下的水,除了切面的交集,终归是殊途。
什么是“异”,与相对比的事物表现不同、状态不同,或内核不一致,为“异”,或也总怀揣着普世价值里不被认可和接纳的观念,便被划为“异”,这里多少有一些高下立判的讥讽成分。所以在这个社会里,异乡人,不完全是一个绝对中性的词汇。
昨天夜里,看到友人在群里发的消息,说还想要一天假期,哪怕这一天要用来干工作的事情也好。“或者就是,明天暂时不要当我自己,暂时当一下别人,比如一个厨师之类的。”在假期结束的边缘,几乎所有上班族都拥有共同的焦虑,但我的这位朋友,提出了“要当一下别人”的想法。
为什么要当别人?她年轻貌美,前途无量,却还是想从这庸庸碌碌的生活中逃脱出去,可她也很知足,只想做“一天别人”,多了不要,少了也不做,就精打细算,刚好是一天。这一天如果拿去做厨师,可能也烹不出几个好菜,面对了厨房的柴米油盐,或是顾客斤斤计较的挑剔嘴脸,不能算是好过,但却要比按部就班的上班要轻松得多。
她是一个总想从生活中逃离的人。在我们的聊天中,时常会出现“落荒而逃”“逃脱”“离开”的字样,好像生活就像某种洪水猛兽,在身后穷追不舍,急于要我们给予它反馈——但实际上,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在第一时间给予积极反馈的,更多的时候,像我们这样的人,只能在被它追上的时候,先想好应对的措施,与它周旋一番,也免不了受它的揶揄和奚落,但只要做好心理准备,硬着头皮,也勉强能应对。而如果应接不暇,或无力招架,就只想逃。
“做一天别人”的想法,就好像把自己包上了一层保护膜,让我们在幻想里成为了刀枪不入的人——我不是“我”,我是一个“局外人”。我的肉体在遵循着生存法则,执行着社会施予我的指令,而我的精神早已游离在外,成为一个“无关紧要的人”,这个人是一个隐世的行者,是一个他乡的来客,“我”的所作所为,实则对身处的这个社会和周遭的环境产生了极其微小的影响,所以精神上的重担,也随之减轻了许多。
我们有时候也会发出感慨,说自己仿佛“跟不上这个社会的节奏”,或在面对一些恶性的紧急情况时,显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与漠然(就好像《局外人》的主人公,在母亲死后,他非但没有哀悼,反而还和女友厮混,做出一些道德层面上颇受诟病的事)。后来我发现,“假装是别人”,好像是一种应激的心理保护机制。
就好像铁遇到浓硫酸,表面会形成一层钝化的氧化膜——这层膜能够保护铁器,让它不会继续受到浓硫酸的侵蚀。我们在遭遇到棘手的、难以解决的情况时,总想“缓一缓”,或者把烫手山芋丢给别人,如果上述办法都用不了,那就只能尝试这样的精神出离法,有点像掩耳盗铃。
因为,肉体是可以被操控的,只要遵循一定的程式和合理的逻辑,撇去心理上的阻碍和区隔,那么相当一部分生活中的问题,是可以得到缓解或解决的。譬如早起不想上班,就把自己想象成执行程序的机器人,“上班”只是写好在你的后台的几行代码,你去执行它,而不要去思考为什么,也不要去思考执行后会产生什么后果,因为产生什么后果,就是程序运行后的结果,如果出了纰漏,那是写代码的人错了,而不是你错了。
然而,在这些虚构的想象中,有十分投机倒把的成分——那就是,我们借别人的躯壳住上一天,或者让别人的灵魂(这个别人,可能是厨师,也可能是保安、飞行员、网红)住在我们的躯壳里一天,在撇清责任的时候,好像也优先选择了那些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去面对。如果我是一个厨师,我就不用在老板叫我写演讲稿的时候,冥思苦想了——因为这不是我的份内工作,我以厨师的精神度过这一天(泡几杯咖啡,打开网页研究食谱,或者打开app开始买菜),也不会对老板一个月后的演讲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。如此例证下去,好像我们一直在逃避,从没有认真地去面对那些难事。
今天,我问她节后第一天上班,过得怎么样。信息过了好一会才得到回复。她说又摸了一会鱼,并且发现了一个摸鱼大法,就是多喝饮料,多往厕所跑。我们愉快地在群里讨论着这些,好像身体里住的真不是一个积极、敬业的人——我们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“别人”,日子对我们来说,只要能混过去就好了。
有些时候我们也会精神崩溃,因为实在找不到可以逃离的方向了,被迫和这个社会产生种种纠葛,成为人际关系里的受虐者(这里用了“受虐”而不是“受害”,因为我想更中立地看待这些关系,不是每个人都要“害”你,但总会有人故意或非故意地“虐”你),我们也只能抱头痛哭一场,只当是演戏失败了,但明天起来,还是要继续演的。
不知道在这个社会里,像我们这样的“精神边缘人”还有多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