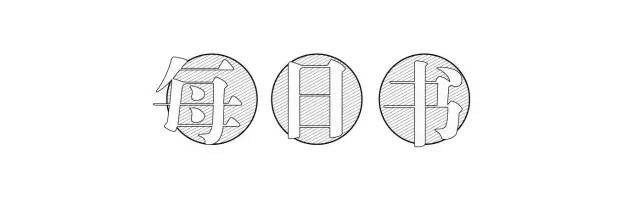这篇文章整合自我2020.5.8-5.10的每日书。这篇文章中的许多观点来自于我的一位名为蔡大力的朋友。他曾经是我的好朋友。
今天的话题更虚无缥缈一些,我想来谈谈世界的毁灭。
当然,“世界的毁灭”只是一个伪命题,因为我们暂时看不到短期内世界毁灭的迹象。所谓的毁灭,只是我想像或期盼中的毁灭。之所以会产生讨论这个话题的念头,实在是因为,我有一个能引导我跳出惯性思维的朋友。
去年有一次,我要去参加一个活动,活动开始前几天,我就感到莫名的焦虑,我开始担心自己在活动上说不出漂亮的、有道理的话,担心我词不达意,担心我不受欢迎——在经历了几天莫名其妙的焦虑之后,我给这位朋友发信息,说:“突然期盼世界毁灭了,这样我就不用去参加活动了。”
也许这就是我和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——我总是期望和幻想它毁灭。如果它果真毁灭了,我便连“假装是别人” 也不必费力了,我直接失去了意识和自主性,成为一坨难以被定义的物质,也再没有人动用权力来对我指手画脚。
过了一会,我的朋友回复我:“初中的时候,我每次不开心,都会用‘人类总是会灭亡’的理由来安慰自己,屡试不爽。默念三遍之后,就会得到一种奇怪的宁静。”
如今,我也用这个理由来麻醉自己,就好像在我不断下落的时候,总有一张网在最下面接着我——这张网,就是我的保底,会让我不至于摔得粉身碎骨、血肉模糊,再坏也不会比落在这张网上要坏了。人类总会灭亡,世界终究会毁灭,在那个时刻,过往的恩怨情仇,能够在物理作用下,极其简单粗暴地获得涤荡。
我们在讨论人类或世界毁灭的时候,都是在隔岸观火,以一种戏谑和调侃的方式在讨论。没有人真的认为在有生之年能够见证它的彻底毁灭,我们所谈论的,只是一种想象中的毁灭。
大制作的好莱坞电影给末日赋予了很多种结局,人类有一万种灭绝的方式——死于陨石下落激起的自然灾害、死于外星文明的入侵、死于某种无法控制的致死率极高的病毒,或被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反噬,被复活的史前巨兽吞食,但总而言之,基本没有一种死法是不瑰丽、是不需要千万成本的酷炫特技的。
但在讨论过后,他说:“很多人想的世界毁灭都是特效爆炸的商业片,但实际上是一部纪录片,甚至就是一段监控录像,像素模糊,声音听不太清楚,人类就这么普普通通地完了。”
也就是说,事实上的毁灭,可能不是一瞬间的事,而是漫长的一年、十年或者一百年,在这个进程中,血腥或者暴力可能只占用了很小的一部分,同样的,也没有那么多英雄主义和侠骨柔情,在世界毁灭的进程条里,我们每天达成0.1%的进程,无数个体化的事件被浓缩在这个进程里,以致于从整体上看,整个进程条经过了数字化的处理,是呈现不出“好”和“不好”的。
继而,他又说:“宏观地去看人类,会觉得这个物种完球了,但凝视某些个体的时候(比如亲友、爱人),又会觉得太好爱了。对人类宏观的厌恶希望它早点灭亡,能减轻自己作为人类群体中一员的罪恶,使自己与那些‘作恶’的人类们区别开,同时对个体的爱,这种联系可以将自己归类以对抗与生俱来的孤独,我觉得这样的摇摆就是生活。”
我希望他解释一下什么是“太好爱了”,他说:“‘太好爱了’比较普遍的表现就是追星,那些‘彩虹屁’就是觉得‘太好爱了吧’之后产生的化学反应的遗留物。或者觉得楼下阿姨卖的肉夹馍怎么那么好吃,而且每次都记得要给我加双倍香菜,真是太贴心了。这种也算。”
“这种摇摆是很普遍的,所以我们同时丧和交社保,同时减肥和喝奶茶。”
但无论是正面的情绪,还是负面的情绪,都是一种自作多情。世界没有所谓的“好”和“坏”,因为每天都有人在打劫、在失去双腿(我们把这些不幸暂且定义成“坏”),每天也有人在做公益、救助流浪动物(我们把这些善举暂且定义成“好”),它每时每刻都处于流动和变换之中,我们所目睹的也只是这方寸之地。没有人能看得到它的每一个角落。
“这种自作多情具体表现为大部分人问:‘这个世界还会好吗”,或者‘人间值不值得’”,他说,“大家在‘会好的’和‘不会好了’中站队、讨论,然后衍生出不同的变种,比如:世界会好、你不会好;世界不会好、我们能好,之类。”
但是大部分人也没有想过怎么去界定“好”和“不好”,因为在A看来的“好事”,在B看来也许糟透了,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,就好像婚姻与新生儿让一部分人雀跃,却让另一部分人头痛欲裂一样。同样地,我们甚至也鲜少为让它变得“好一点”或者“坏一点”做出任何举动,或者说,我们的举动是难以被定性的。
这很正常,我们看起来多么乌合之众,但我们本来就是乌合之众啊。
所以,当我回看这个“世界之毁灭”的命题本身,我发现它虽然令人情绪激昂,但却充满自私的猥琐想象。我之所以期盼世界的毁灭,实在是因为我自己过得也不怎么样,阴暗的心理让我发出这种诅咒,希望自己不是被这个世界遗弃的人,如果是,那希望其他人和我一样被遗弃。但反过来想想,如果有一天我志得意满、春风满面,我还希望世界毁灭吗?
写到最后,我发现我忘了提这位和我对话的朋友的名字——他叫蔡大力。上述的对话基本上都出自我们的聊天内容,只有略微的删改。
蔡大力说,带给他平静的“人类总是会灭亡”的咒语后来失效了——“因为我发现,我同学穿的一双耐克要四百八,比回力的20倍还贵。”
这咒语最后就变成了“人类总是会灭亡的,可是他死的时候穿着四百八的耐克”。
整个人被打击,无法自洽。